□蒙成花
特别喜欢晚秋时节。清晨,我站在屋顶极目远眺山坡上的那些野杏树和山花、杨树、沙棘等,被霜露侵袭后变成了橘红、酡红、浅红;山谷里金黄色的铁线莲、褐色的毛茸茸的狗尾巴草、猫儿眼等,仔细瞧,从他们的根部又冒出了新芽,它们恣意萌生着、茂盛着,想把这壮美的晚秋留住。
农历九月中旬进入了秋天的第五个节气——寒露。天气慢慢变凉,昼夜温差大。寒露也是个撩拨思念的季节,我干瘪的思绪在那霜露般的月色中变得柔软、湿润起来。
穿越时光,母亲的土坯泥屋的屋檐下挂着一串串切成薄片的萝卜干,一串艳红的辣椒,父亲的一串烟叶。土墙缝里塞进了布兜,里面装了花籽,有旱金莲、蜀葵等。母亲把胡萝卜切成细丝腌制花菜,用食醋和白糖腌制洋姜。日子清贫,鸟鸣婉转,月光清澈。乡间的小路铺了厚厚的金黄色树叶,我跟着姐姐们踩着溶溶月色去村小学操场看电影。母亲是闲不住的,晒在屋顶上的胡麻经过风吹雨淋的沤了,拾起月光,抡起连枷“啪、啪、啪”捶打,光溜溜的胡麻籽簸去了糠皮,炒熟碾碎了做成油花,又叫花卷馍。日子在细碎的光阴中慢慢流淌。
浸霜的三色堇、美人蕉枯萎了,那些“肉肉们(多肉植物)”,如紫米粒、月亮仙子、吉娃娃等,夜晚忘了搬回屋里,天放亮时它们被薄薄的霜露覆盖着,露出了尖尖的叶子,如婴儿的胖嘟嘟的手指,当煦暖的阳光铺满院子时,霜露融化成了晶亮的水珠,挂满了肥胖的叶瓣,晚秋的光照虽短,但“肉肉们”舒舒服服地铆足了劲儿酣畅淋漓地舒展着身躯。
三色堇像清纯透明的村姑,憨实温柔,枚红色的矮牵牛刚刚绽放时婉丽明艳,落了一层薄霜的矮牵牛在月夜里婉约成一位风姿绰约的女子,霎时让我心神荡漾。蓦地,映入眼帘的,是一株不起眼的白色打碗碗花,它从屋檐下的墙面瓷砖缝里冒出来,默默地延伸茎藤并开着几朵小花。在野外,它们披着厚厚的霜露呼啦啦覆盖了山坡沟坎。它耐寒耐旱耐瘠薄,虽然适者生存的法则太严酷了,但它还是不择环境的优渥与否,默默地萌发、抽枝、分蘖,拧着脖子爬蔓绕藤。传说打碗花是神仙送给凡间用来辟邪的花,因此,她的花语是“恩赐”。她的俗名叫“狗儿蔓”,我把这字面意思理解为它的茎藤柔韧,不择土壤气候环境疯长的意思。我特喜欢狗儿蔓这名字,可爱又皮实。虽没有养尊处优的盆景那么妖媚,但她骨子里透着一股韧劲。
几朵旱金莲(也叫“旱荷花”)的茎藤攀绕着一丛金灿灿的黄金菊在煦暖的阳光下开得肆无忌惮,弥散着浓烈的芳香,它跟黄金菊都耐旱耐寒。阳光倾泻在圆圆的叶面时,霜露成了晶莹的水珠,微风拂过,水珠滴溜溜滚落。
寒露是二十四个节气中最让文人墨客销魂荡魄的节气。白居易的诗把寒露描绘得情景交融,荡气回肠。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零。兰衰花始白,荷破叶犹青。独立栖沙鹤,双飞照水萤。若为寥落境,仍值酒初醒。
白居易描写寒露的诗显得哀婉、凄楚、空灵。但我眼中的寒露,被寒露浸染后的植物多么清丽又温婉。
半轮上弦月升起时,那溶溶月色下的旱金莲和黄金菊披了一层薄霜,显得冷艳、绮丽。月色和霜露将我裹挟了,我在张若虚“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的诗句里沉醉。
一位作家说过,当心静下来时就闻到芳香。观赏一株被霜露浸染后的花时内心激荡着欢喜,所有的坚硬和冷漠都会变得柔软起来,再也没了心浮气躁,享受独处时内心静得能听见一朵打碗碗花以及所有卑微的植物内心透明的哀伤。它们不想在结板的土壤里蛰伏,它们还在月夜里蠢蠢欲动,歇斯底里地盘根错节。
像一棵植物那样,心存一粒阳光,干净、柔韧地活着。活得豁达、通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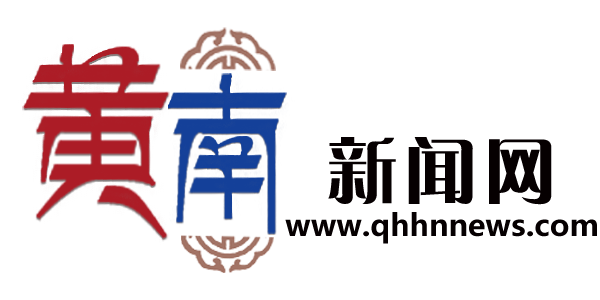

 青公网安备 63232102000018号
青公网安备 6323210200001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