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隆马阴山采访途中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编者按
在新闻采写方面,青海老报人、老作家王文泸有着丰厚的经验和独到的观点,他严谨、敬业、执著的职业精神为青海新闻工作者树立了榜样。王文泸在新闻报道上取得的成就,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把鲜活的新闻事实、现场气息与文学的审美表述完美地嫁接在一起,他的深度报道,尤其是人物通讯,每出一篇,都堪称范文。
融媒体时代,我们对新闻资源的挖掘利用,许多时候还停留在表层,远远没有“物尽其用”“循环利用”。怎样深度挖掘和利用新闻资源,王文泸以他的众多作品,回答了这个问题。他给予新一代报人的启示不但没有过时,在提升“四力”方面,还有着比一般作家更为贴近的经验和借鉴作用。
记者节到来之际,本报记者对王文泸进行了专访,让我们一同来聆听他那清风般有益于我们眼界和心灵的言说。
记者:您是青海新闻界的老前辈,也是青海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位作家。以我们的眼光看,您很特殊,因为您在两块完全不同性质的天地里同时耕耘,都很成功。且不说您的短篇小说、散文和随笔,即便是您写的新闻通讯《烛光奏鸣曲》《钢铁是这样炼成的》等,都完全可以作为范文来读。以您的经验,做媒体工作与从事文学创作,两者有互补的效果吗?
王文泸:我从参加工作一直到退休,基本上都在媒体工作。至于文学创作,说到底也还是个业余爱好者,谈不上有多少成就。但是从事新闻宣传与文学创作,这两者之间确实有着可以互补的必要,对于这一点我还是深有体会的。无论是我当记者、当编辑或者是当报社领导,新闻这个职业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为我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观察社会的平台,为我接触实际生活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开阔了我的视野。吃新闻这碗饭,接触面肯定会宽一些,对国计民生、五行百业,自然要去关心、去了解,而且,只要你是个有心人,只要你不满足于仅仅用新闻的眼光去掂量已经获得的素材,而是注意到了某些素材还有转化为文学的可能,那么你的收获将是双倍的。我曾经说过,我的不少散文随笔就是文学对新闻的二次发现,或者说是二次利用。这是从事新闻采写带给我的好处。但是,也不是所有的新闻素材都能被文学利用,这要看素材本身的价值和采写者的思考角度。另一方面,一个记者如果有比较好的文学素养,毫无疑问会为新闻写作产生助力,让新闻表达更加准确、鲜明和生动。如果写的是消息,那么这个消息在文字上一定是干净利落的,没有半句废话、没有词不达意,每一个标点符号都准确无误;如果写的是通讯,那么这个通讯必然是新闻视角、文学语态,对读者更有亲和力。
以上说的是新闻和文学的互补作用。但我们谈这个问题,不能只从技术角度去谈,只看到互补的实用性;我们更应该从新闻和文学各自的本质和各自的局限性上去看两者的关系,才能说清楚互补的意义。我们都知道,新闻的本质是信息,它追求的是传播速度和覆盖面积;文学的本质是艺术,它追求的是审美价值和久远的影响力。我有篇文章叫做《记者的眼睛和作家的眼睛》,谈到了这两者的关系。
记者的眼睛习惯于盯着新闻事实,却容易忽略隐藏在新闻后面的完整人性。因此新闻对生活的表现一般来说较之文学作品虽然更直接、更具体,但也更表层。在社会变迁过程中,饱含着生命个体复杂感受的生活在记者笔下常常被忽视。当我们试图从已经成为历史的新闻报道中去了解人性真相时,所看到的人,其实多是为新闻事件作证的人,很难看到有自己灵魂的人。无论是看1年前、10年前或50年前的新闻,都是如此。即使是专门写人的通讯,新闻也不可能去完整地表现人性的各个方面。所以说新闻有它的局限性。
我以前谈到过这样一个例子,是发在报纸上的一张新闻图片。记得图片说明是“随着生态保护政策的实施,玛多县的部分牧民从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山草场搬迁到县城附近,住进了整齐划一的移民新村,过上了幸福生活。”照片上是老少三代牧民,身穿簇新的藏服,并排行走在“整齐划一”的新村巷道里。按一般新闻标准看,这幅照片它讲诉了一个新闻事实。但从文学的角度看,有问题。问题在于:在记者眼睛里,生活显然被简单化了。简单得只有“幸福生活”这样一个概念。纯新闻的眼光使记者无法看到这个事实后面还有一个巨大的认知空间,那就是,对任何个人或群体来说,构成“幸福指数”的,除了物质生活条件外,还有另外一些因素——比如精神的归属感、对自身生活能力的信心,他与所处文化环境的融合程度等。要看到,生态移民是事关国家生态安全大局的重大举措,也是在生态与生计之间作出的艰难抉择。对牧民来说,面临两难的抉择:要么继续与高寒缺氧为伴,与不断退化的草场为伴;要么彻底改变生活方式,进入城市。这种矛盾在被搬迁的牧民内心中,形成极为丰富的感情动荡和观念冲突。对城市生活的好奇、向往和疑虑是一面,对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难以舍弃、对蓝天白云牛羊的留恋则是相对立的另一面。相对于城市人,农村牧区的人更保守一些,故土难离是一种基本情结。当他们坐上满载家当的车辆,最后一眼告别牧帐、告别熟悉的山脉、河流的时候,我想心情一定是很复杂的,不可能简单得一路上只想歌唱。
但是记者的眼睛一般看不到这些,就事论事的思维习惯严重地局限着记者的视距。他们不太习惯于像作家那样从人性的角度分析生活。如果做到了,这幅新闻图片所传达的信息深度就会延伸,这幅照片的说明也许会写成这样:“为了让严重退化的高山草场得到休养恢复,在政府的苦心动员和周到安排下,玛多县部分牧民挥泪告别雪山草原,来到县城附近的新村定居。未来,他们从生活方式到情感将经历较长的适应期,但是为了大局,他们勇敢地接受了生活的挑战。”
这就是新闻的局限性。
作家的眼睛就一定是准确的吗?也未必。作家的眼睛喜欢越过新闻事实,按照自己的审美经验和价值判断去表现生活。这样的生活再现,艺术上可以打造得很美,但与实际生活一对照,发现似是而非,很容易露出破绽。这种情况在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
所以说,无论是新闻还是文学,要想避免过于肤浅或过于片面,最好兼有记者的眼睛和作家的眼睛才好。
记者:据我所知,各种文化层次的读者,都爱看您的作品。就像我,甚至把您的书当作夜读必备,时不时地翻上几页,沉浸到作品所表达的意境当中。客观地说,您的创作数量不是太多,但引人注目的是您作品的高品质。您认为,您的作品经得起读者再三品味的原因是什么?
王文泸:我想,这主要还是因为心里有读者。作品要想打动读者,真诚是绝对必要的。绝不要想取巧。也不能自说自话,完全不考虑读者。我从来不随随便便地写。动笔之前总是在问自己:是不是值得一写?读者会不会感兴趣?如果没把握,就坚决放弃。如果站在读者的角度,当我们打开一本书的时候,总是有所期待的。读者期望作者给他提供一个新的认知空间,获得新的思想启示和艺术享受;如果不能,他希望作者让他看到自己没有经验过的陌生的生活内容,满足阅读的新鲜感。如果还不能够,读者希望自己也同样经历过的生活被作者挖掘出不一样的意义,或者说自己的某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理被作者一语道破,也就是人人心中所有、人人口中所无的东西被作者准确地说出来,从而引起共鸣;如果还不能,最起码,读者希望作者的语言文字别具一格,绝无刻板枯燥的表达,使阅读过程变成一种享受。
出于这样的考虑,我在选材和表达两方面都比较下功夫。选材方面,别人写过的题材绝不再写;别人用过的角度绝不再用。尽量不和别人撞车。表达方面,我追求一种朴实自然、娓娓道来的风格。我一贯苛求语言的准确。既苛求自己,也苛求别人。长期从事编辑工作,养成了对文字表达的“敏感病”。审读来稿时,只要有一两处用词不贴切,就知道作者的文字功夫欠火候。在审读一些有相当知名度的作家的来稿时,我发现,不少成熟作家的作品竟然还有那么多语法、逻辑和修辞上的毛病,一抓就是一大把。这当然不能成为否定他们作品的理由,但是文字有那么多硬伤,作者毫无觉察;或者因为名气大了,完全不当回事,这毕竟是很遗憾的事。这样的作家真不是一个两个。
记者:您的作品题材非常广泛,而且思考非常深入,一些常人熟视无睹的现象,在您笔下经常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发现,这跟您的阅历有关系吗?或者是一种习惯?
王文泸:这跟阅历有一定的关系。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经历了那么多次社会变革,价值观念、生活观念乃至审美观念,不断地处在迷茫和更新的状态,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特点。但这个只是共性而不是个性。就我个人而言,从走出校门到退休,除了有短暂的两三年在政府部门工作,其余几十年都是当记者和编辑,而且有十几年时间在基层,这让我有很多机会深入到农村、牧区、部队和工矿企业。对于最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不仅有直观的了解,也对他们的生命价值常常产生思考。二十来岁的学生,在今天,大多还是撒娇的孩子,而在交通和生活极为艰难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二十岁出头的我,竟然受命带领一支人马,跋山涉水,远赴甘青交界,冒着生命危险,去草原纠纷地带支援青海人。这对一个还没有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是多大的精神压力和心理考验!但今天回头想想,这样的经历无疑丰富了我的人生。要不然我这一辈子太单调了。我日后搞点创作,题材比较广泛,就跟这种经历有点关系。
当然了,不是所有难忘的经历都值得去写。如果它仅仅是生活经历的记录,那还不如直接去写回忆录。关键是要从沉淀了好长时间的素材中发现点什么。如果有,在哪里?挖掘不出来,只有放弃。如果有一天发现了,这个陈年故事就活了。
同样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大家都司空见惯的生活现象,如果思考能深入,就能写出点新意。比如,一个很短的散文《灼热的手心》,就是写了在别人眼里也许根本不值一提的小事:割麦子的镰刀把子。我从这件小事看到了两个社会层面的变化:一是手工业时代已经结束,社会已经进入逐渐成熟的工商业时代;二是随着社会分工的泾渭分明,城乡关系发生了变化。我的另一篇稍长点的随笔《此岸和彼岸》,也是从人们熟视无睹的现象中看到了社会的一个深刻变化:那就是来自农村的“新城市人”的出现,如何改变着今天的城市,特别是农村人向城市人的转化过程中,他们的心理、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价值观所面临的挑战。
记者:您的作品里很少有风花雪月一类的题材,这跟兴趣有关吗?
王文泸: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兴趣问题,这是一个文学态度或者价值取向问题。大家都知道风花雪月自古以来就是永恒的题材,也是一个叫前人写滥了的题材。今天以及今后,还会有人乐此不疲地去写,这很正常。但是写出新意很难很难。鲁迅曾经调侃说,如果让他写风花雪月,他会写“风高放火天,月黑杀人夜”。就我个人而言,尽量不去写过于自我的东西。尤其不太写花花草草、小情小绪的题材。总觉得那类东西虽然可以做到精致,毕竟渺小,没多少分量,而且远离现实。我有一篇很短的散文《火烧芍药酒牡丹》,是唯一纯粹以写花为主题的。但我不甘心就花说花,文章末尾还是触及到了一个哲学命题:“违时而花,为造物所忌。”想以此来稍稍增加一点分量。
记者:我相信,无论是写新闻作品还是从事文学创作,写作的人都会遇到表达障碍,即使是老练的记者或者作家。当某一种认知、某一种情绪,或者某一种价值判断,在心中已经酝酿成熟,但就是写不好,总是写不到位的时候,这种感觉尤其强烈。但是我们看您的作品, 好像并不存在这个障碍,无论写什么都是举重若轻,而且恰到好处,好像更改一个字都不可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字功夫吗?
王文泸:说到表达障碍,所有的人,无论是写作的新手还是老手,都会遇到这个问题,这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但是克服表达障碍的过程,恰恰是表达能力提升的过程。写作的人通常遇到的困难主要有两个,就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的: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或者换一种说法,叫做心中了了,笔下难明。这是所有写作的人都会遇到的障碍。这实际上是两个障碍,涉及观察能力和表达能力两方面的。
一个人的艺术感觉,或者说审美感受能力,主要来自于先天。有些人天生审美感受能力强一些,有些人天生弱一些,这个情况在后天比较难以改变,就算你读了大学中文系,取得了博士学位,也未必能改变这个状况。但一个人的表达能力,通过后天努力还是可以提升上去的。十多年前,在省作协组织下,我们与青海师大人文学院的学生有一次现场对话。我提了一个问题,或者说是谈了一个观点:我们选择读中文专业的意义是什么?当然,读中文系,系统地学习中外文学史,了解历史上的文学现象,懂得文学鉴赏的基本知识,掌握文学批评的一般原则和方法,等等,这些都是必须的。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解决我们的文字表达问题,如果读了中文专业,你的文字表达不能比一般人更准确、更生动,或者如韩少功说的,你没有能力用文字表达出“最真切的感情和最精微的心理”,那你这个中文专业在一定程度上是白读了。
文字要写好,必须舍得下功夫,慢慢地去磨。我以前也谈起过这个体会。有的作品一遍一遍地修改,到了最后,吃饭睡觉的时候还在琢磨,七八千字的长稿,闭着眼睛能默读下来。默读的过程中还会发现,某一处标点符号不准确,应该把逗号改为分号。半睡半醒之中想到了一个很妙的比喻,会爬起来拿笔记下,生怕一觉醒来又忘了。
但是我也意识到了,唯美的追求没有错,打磨和锤炼也没错,但不能过分地雕琢。我早期的小说和散文,有时过于修饰,留下了雕琢和斧凿的痕迹,显得不够自然。比如有些句子为了追求生动,我喜欢在主语前面加上比较长的定语,谓语前面加上比较长的状语。这个定语部分和状语部分就往往属于过度修饰。后来我自己认识到了,就有意识地去改变,比如在用词方面绝对不用怪异的词汇,避免陈词滥调。尽量少用形容词和副词,多用行为动词;少用长句,多用短句,等等。
“精神到处文章老,学问深时意气平。”这是清朝诗人石韫玉的名句。我虽然没什么学问,但是意气早就平了,表现在文字上,就是逐渐趋向于平实的风格。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基层广播站当记者,天天写广播稿。这段经历让我认定,好文章一定是读来上口的。如果读起来疙里疙瘩,说它再有文采,我也难以认可。
记者:读您的作品的时候,无论是叙事、抒情,还是思考、追问,总觉得文字里充盈着自信、安详和放松,而绝没有枯燥乏味的表达,请问,这是您追求的文字风格吗?
王文泸:这个问题我们刚才的讨论中已经差不多都谈到了。首先我写作的过程就是和自己心灵的一次坦诚的对话,写出来以后,目的是和读者交流,得到读者的认同,而无意去充当所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就让读者感到轻松,其次,笔下的轻松也确实来自于对表达能力的自信。
记者:我们注意到,您后期的创作中有越来越多的文言作品,而且是非常地道的文言文。这在当代作家中极为罕见。没有深厚的文言文素养,写不出像《买针记》这样的作品。这篇作品在网上纷纷转发,有人甚至认为这样的作品才可以传世,够得上经典佳作。的确,如果不署上作者的名字,读者不会相信这是当代人写的文言文。请问,您这么执著于写文言文,仅仅是喜好吗,还是有别的用意?
王文泸:我尝试着写一写纯文言作品,不是主张复古,而是为了把白话文写得更好。文言对白话有滋养作用,后劲很大。五四运动以后那些大力提倡白话文的学者,哪一个不是有深厚的文言文素养的人?有文言基础,再写白话,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比如昌耀的诗。我虽然不懂诗,但感觉到他作为现代诗人,用词有时候非常古典,这样的词语镶嵌在白话的诗行中,像珍珠一样养眼。
白话文成为普遍的书写方式,才不过一百多年,还不能说是非常成熟,虽然出现过像老舍、沈从文、汪曾祺这样的白话文圣手,能够把白话文写得出神入化,但从整体上看,白话文写作中,拖沓、拉杂、随意,处处口水的现象,还非常普遍。这还在其次,更让人焦虑的是,白话文的水平这些年甚至还出现倒退的现象,主要是语言的粗糙化和粗鄙化。这大家都感觉到了。网络的出现和键盘的使用,让书写变得极其容易,进入了被人们称为语言狂欢的时代,但一定程度上也是语言垃圾化的时代。大量被网民随意创造和随意改造的词汇来不及扎下根就被淘汰了,朝生而夕死。而文言文从先秦算起,到民国初年,发展已经有两千年,积累了足够丰富的语法技巧和修辞技巧,非常成熟了。比如它的典雅和凝练,永不过时。
其次,由于汉语特殊的结构,很容易形成对偶和排比,这在世界其他语种中是没有的。对偶和排比造成朗读时的音乐感。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岳阳楼记》和《荷塘月色》。先不说这两部作品内容有没有可比性,我们只从朗读效果比较,哪一个更有音乐感,不是明摆着吗?像我写的散文《青海的山》当中,写到雅丹地貌:“极目望去,这些山丘如猛兽蹲伏,似宫阙林立;又如战舰列队,疑兵布阵,号令不发,电讯静音。忽而风动沙起,丘阵内异响呼啸,怪声隐约,森然可怖,魔鬼城由此得名。”这一段四个字一组的排比句,你说它是白话吧,它们明显地带有文言的特征;你说它是文言吧,放在通篇白话的文章当中,并没有什么违和的感觉,相反还精炼了不少,我也尝试过,假如把这种场景描写转换为白话,不仅篇幅会大大拉长,而且文字结构会变得松松垮垮。
所以说,文言文特殊的艺术美感不可能由白话文代替;从实用性讲,这种传统技巧的丢失,给现实生活中时不时地造成被动。因为即使到了今天,还要经常要用到文言文。比如,铭文,碑记,墓志铭,祭文和楹联,都适合于用文言形式来撰写。
尤其是楹联这种形式,它在最广泛的大众接受面上,把文言的一些特点保留下来了,一直延伸到今天。楹联以简短、对偶和朗朗上口的形式,把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的丰富感受浓缩在方寸之间,取得了以少胜多、以简胜繁的效果。但是如果没有文言文写作的素养,无论如何是写不出好楹联的。当这种需求偶尔提上议事日程时,经常使当代文人们捉襟见肘,无法应付。所以说,我尝试着练习文言文这种高难度的写作,也是为了弥补自己这一方面素养的不足。尽管为时已晚。假如从青年时代坚持学习和练习,到了今天,真的可以成为独家绝技了。
记者:写作对您有哪些改变?带给您什么样的快乐?
王文泸:写作并没有改变我什么,最多可能对我的气质有些好的影响。写作给予我的,是创造的快乐,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快乐。我们所有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其实都是被动的、被制约的,有时甚至是很无奈的。只有进入了创作活动,我们才是主动的、自由的、充满了创造精神的。我们用精美的文字创造的东西,甚至可以奢望它是不朽的。这就是最大的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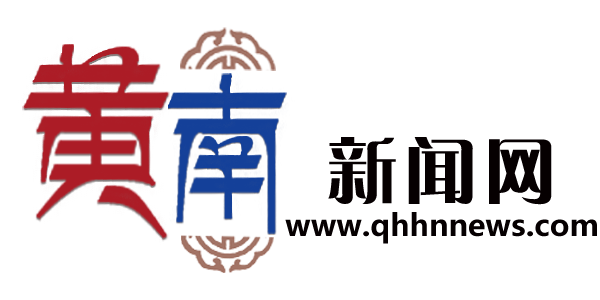

 青公网安备 63232102000018号
青公网安备 6323210200001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