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间,听得最多的一句话:“惊蛰寒,冷半年”。偏巧历年这天,多是立春以来最冷的一天。
地气升腾,前后又飘过几场春雪,空气不燥,张开的毛孔感到有些冷。
花园里,黑白喜鹊、灰褐树鸽、花麻雀逡巡,或叼一两颗去年冬青残留的红果,拣尽寒枝,忙慌着心事,敷衍叫两声,飞远了。搅挠了枝条正在继续的春梦。
春雪到底擦亮了万物的眼。猛然回头,去年的冬青红果,映着碧桃,像戏里手掌心擦了一抹胭脂的丫鬟春红,探头探脑。
龙抬头的日子刚过。
为了惊醒被腊八粥糊了一冬的心眼,更为了安慰我们撩乱了一个正月,突然又无所事事的嘴巴,母亲早在前两日,穿了旧罩衣,苫了头巾,捂了口罩,在黑沿大铁锅边,用沙土炒了专门余留给我们磨牙的申中特产马芽蚕豆,俗称大豆。
伙房里火舌舔着锅,土腥气乱窜。铁锅遇上火,沙土遇上豆,蚕豆在锅里“跳蹦蹦”。如夏天骤雨急落在院坑里,无数个旋涡溅起的“跳珠”。如苏轼《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里的雨:“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黑铁黄土里的“跳珠”,声音裹了土气和火气,先一阵“扑哧、扑哧”地沉闷,又噼噼啪啪地暴躁。接连一串爆响,有蚕豆跳出锅,“扑”的一声,一根弧线落到灶台或地上。再噼啪,再大珠小珠,炒熟的蚕豆晾摊了一地,七八斤,外焦内黄。
闲人来串门,母亲从箕中舀出一瓷碗,放炕桌上供人“谝闲传”(聊天),来人调侃一句加“料瓣”吗,然后笑着捏一颗,脱去焦皮,塞进嘴里,“咯噔、咯噔”,咬豆声不绝。
给牲口加的偏食才叫“料瓣”。春耕下套驾铧犁地,草料不够牲口出大力,于是那些上年秋收时,不能入口粮或留种的稗麦麦或苦豆,派上了用场。食槽里隔三岔五添加稗麦、苦豆给牲口吃,俗称加“料瓣”。
乡人见惯天灾人祸,而性情豁达。又自知土里刨食者如己,概与牲口无二,故言语幽默,以解闷逗乐自嘲为日常能事。
母亲的说词是,“二月二,‘憋’虫儿”。憋,是动词。意思是把蛰了一冬的百虫惊醒,所谓惊蛰。
“蛰”的字典在乡下,乡人是它生生不息的土壤,冬天是乡人翻它的高光时刻。
有人袖手晒墙根牛吹得正起劲,有人偏偏不识时务,扬言要回家吃饭,同伴就撂一句“大冬天的吃啥饭着,你蛰哈呗”。
“你蛰哈(哈,语气词)”。说着拍拍土走了。
到了做饭点,女人一边挽袖,一边笑着幻想:“人如蛇一样,冬天蛰(哈)着,不吃不喝,该多好”。女人不知道蛰伏动物还有很多,却知道蛇。
有人生病卧床多日,忽一天痊愈出门走动,见者迎上去高兴喊一声,你蛰罢醒了吗?双手握住蛰罢人的手。
一群小子正疯的起劲,弟弟吸着鼻涕磨人,大孩唬弄小孩一声,你蛰哈去。小孩子一脸丧气,哭着蛰到家去了。
城里每年惊蛰前后,总有那么几个人,像影子一样,不知从哪条缝里飘出来,走街串巷,挑担呼告。
“收长——头发哎,头发(音hua)”;
“磨剪子哎——戗——菜刀”。
或南音一样隔空悠长,或北腔一样铿锵悦耳。犹如乐谱里的渐强或减弱,撩拨贾平凹笔下的人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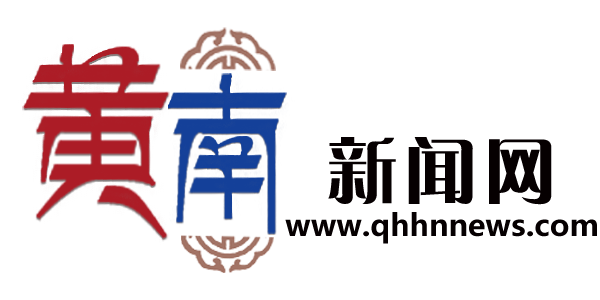

 青公网安备 63232102000018号
青公网安备 6323210200001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