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钧的很多文字,很像是郊野的刻石画像——首先是文化和文明的孕生物,有着铭文勒石的质感和品相,细究,却又觉得与郑重的路标和指示牌存在巨大的差异。怎么说呢?他的文字和文学的趣味因着郊野的自在和沉着,而将书斋隔窗听雨呈现出“修竹齐高树”的自然的状态来。
马钧曾舌耕大学课堂,现为省报文艺板块的执掌者。以上仅仅是铺垫,马钧更是一位秉烛夜游、谈龙说虎的慧心人,是以多种艺术形态和生活材质得取诗魂光焰,并且尽一己之力将诗之明亮和邃远传播于四方的“养蜂人”。其实,他还是一位偶尔使用分行,在更多时候以非诗的形状豁显诗核的诗人。
这样的诗人,往往沉溺于他人难以猜度的欢乐,蹀躞于郊野,以获得天光水色隐秘的激荡。马钧的文学志向,趣味,形制,很早就显露出郊野独行沉吟昏晓的“体气”。十年前,马钧出一册文学评论和艺术品评的论著,名曰 《文学的郊野》。他的执拗与绵厚、清简和肥腴,于这本书中有着令人深刻的表现。可以想见,似如马钧般的握管者,其乐独有;更多的时候,朋友们也未免替他可惜——大雅几人听?
机缘就这样来了。青海作家李万华的锦绣文章的文气、文采,激引马钧先生共赏雕龙文心,同探诗艺构理。我读“马氏文通”别册——《嘤鸣友声:致李万华书简》,直有从聆听独乐而观对舞的感受。而此书编舞超然,种类混搭,舞步多变,却又脉流清楚,是跨越了批评和文论的边界,在随笔的原野驰息的灵兔和回归的野马的自在展演。被马钧以“精灵古怪”为线路细品慢鉴的李万华,反映出论者其实是另一种相征的“精灵古怪”。论者与被论者的相互激荡(更多的是李万华对于马钧的激荡),引申出审美“手谈”的意蕴、美感和互嵌。这是一次稀见的双向挑选,其手语、舞姿、意态,莫不因为重华繁绽而格外“酷飒”。这样的书写,基于论家和作家的同情共感,恰如两人行于暮色郊野的灵息互通;而郊野也在这样的吸引、辨识、欣赏中,从个体中复活,展示出颅顶天空的浩瀚和身边万有的生动。
我之所以用比喻表达马钧文章的特质,以及对于李万华的辨认(马钧于此明白地判断“李万华已是青海作家中的翘楚,在全国优秀作家中也是星辉难掩”),是因为“比兴”从来是汉文化表达方法和认知事理的核心。在此,马钧通过比较,选择了年幼于他十多岁的李万华;随之而引譬连类,兴致勃勃,舌灿万华。读其文,马钧借李万华的文章腾挪翻转,速览静品,从文华诗心而文统革新,从风土地理而个人经验,乃至在更为宏阔的空间代言指导,调息运气,织就了多材质、多技法的立体长卷堆绣。换句话说,马钧借与李万华的深研细赏,又一次完成了自我“分身术”——是一个马钧与另外一位或者多位马钧的“辩经”、问难和会心一笑。然而,《嘤鸣友声:致李万华书简》生起又绝非是马钧独舞。在笔纵墨涌之际,李万华的文章如同药引,如同铜镜,是酵酿马钧从新的路径再做郊野之游的光影。《西游记》第一回中便说道:“料应必遇知音者,读破源流万法通。”马钧遇李万华,真有读破源流通万法的意思呢。
于是,我们看到马钧不仅屏息于李万华的精神气质,瞩目于作家美质的构画气韵,甚至像个从《隋唐演义》《大明英烈传》中走出的通阴阳五行,知易理之变的堪舆先生,连作家的名字也作为暗通审美的密码,而置设于天象人文考度一番。看上去,这种烛微探幽近乎于癖,实则是将李马二位的文字都显影于汉文化的深广背景中,复活那些几近于弃、几近于忘、几近于不能的感受和表达力。于是天象气候,地理草木,风卷云舒,书册管弦,影碟唱机,往事近影,纷至沓来,与心境笔意,枝节勾缠,蓬生蔓衍,历时共时,重绘人文,形成了李文马说的奇观。这双重的文心诗眼,在阔大而活跃的传统巨流的衬映下,同时展现出视野的宽度和体察的深度。这种书写的宽博深远,暗合、并且也在改写着亚里士多德的一个判断:“历史记述已经发生的事,而诗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在今天,史与诗的互融,情与境的同构,已经成为各式艺术表达的常见;但是,所表达的形制和指向,仍然清晰地成为二者泾渭的分界。如何跨界、越界、调取花粉丰富味道独具的文学之蜜、艺术之蜜,马钧在摩赏李万华的文辞中,透露出了一些秘密的信息。在我看来,马李二人都是熟谙将可能之事写作历史,或者将历史写作化为诗性可能之事的圣手——这里的历史,因为是特指个人的际遇、经历和经验,而在一种可逆的观望中,生成了类似崖石胞苔,珠串包浆的质感和光泽来。如此,马钧论李之堆叠、回旋、类聚,可称为是辐辏的探寻和兴叹。只是,马钧的“美的历程”,是偏好于时空的过渡地带——于地理来说是郊野,于时候来看是晨昏。正是在交接换替的所在,一个人、一个人的踪迹印痕,才于难显之处标明得清晰。马钧喜悦于天光将明或者暮色苍苍,这时候,他的神思灵感最为充沛,他的语言的成色最为醇厚。《嘤鸣友声:致李万华书简》分为十章,其中四章写于卯时,亥时写出三章,辰时两章,酉时一章。此中既有生活和工作的限阈,又何尝不是生物钟神秘的设定呢?马钧也出色地把握了时机,在这个为尼采、波德莱尔、克尔凯郭尔、鲁迅等先贤钟爱的“一天的郊野”,他让自己的文章如同晨光晚照的景象,呈现出别样的色彩。相应的一种情况是,很多美妙的艺术品并不适合在强光下欣赏,倒是在有几分沉着的光线下,反而能够焕发出饱满而灵动的声响。马钧之于李万华文章的注视、倾听和理解,恰如在郊野的舞台上,两个灵魂的遇合、交流和酬唱。其间,主体观念、情思模式、场所感知,移形换位,颇有“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的感发和感动。我以为,这个再阐发、再塑造的过程,接续了中国早期文学“诗意创造冲动的流露,其敏感的意味,从本源、性格和涵蕴上看来都是抒情的”(见陈世骧《中国的抒情传统》)的脉流,而马钧的文思情理并织,宏微共举,物我同在,既是对于李万华知音弦动,也是作品与评论、文本与本文的文学激荡。他,他们穿行于昏晓的目光、步履、行姿,本然地带有几分孤独的味道,可也是这几分寂寞,愈加显示出沉思之美的珍贵和耀目。台静农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中论及杜牧诗时准确地写出这种认识:“……而寂寞当时,其磊落抑郁之怀,不觉地流露出来,寓呜咽豪放,寄清峻为秾丽,往往令读者低徊感激,有不尽言外之意……”
我是在“低徊感激”中,几次体会那“不尽言外之意的”。我从马钧的文章中,读出了新鲜而苍远的李万华,也读出了一个文学烛照者的形象。回到拙文初始,马钧的社会和精神的多重身份,似乎是他以浓度极高的情感认同、审美认同,与李万华对谈共舞的动能之一。我是说,在这里存有一位作家对于另一位作家坦荡欣赏的美好品质。实际上,在青海有很多作家得到过马钧诚挚的邀约,并在“马氏文通”的视角下获得超越知识和技艺的鼓励。我也是得到过马钧惠赐心香的朋友之一。
20世纪80年代初,瑞士文学批评家让·斯塔罗宾斯基先生,在接受法国《文学杂志》的访问时,提到了他的前辈、法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阿尔贝·蒂博代在1922年写下的六篇文学批评。这几篇文章是由蒂博代的讲演而来,斯塔罗宾斯基重提60年前已如郊野松柏的文论,是因为蒂博代关于“自发的批评”“职业的批评”和“大师的批评”的划分和阐释,学理功能仍然强盛。马钧的职业和修养可以说是三者俱占,而他创造的热情、越界的能力,则倾向于大师批评中的“审美的批评”。这样的批评要求作者涵葆对于艺术创造力的深刻同情,既是批评的分析,也是审美的创造。落实到调弦定音,则有“既不以法缚,亦不以法脱”的品相。实际上,这就是斯塔罗宾斯基所期望的,在三种批评上混生的更具生命力的样态。这位瑞士的教授,将这样的批评称为“随笔”。
“熟悉天性,热爱天性,尊重天性,由此产生一种热情,此乃寻美批评之真正的必要性”。这句话是蒂博代讲给批评家的。我们将之理解为讲给作家,甚至是所有人听的,又有什么不适合呢?
“建强,如啄木之鸟,开始剥啄有声吧。”这是十年前马钧赐《文学的郊野》时写给我的赠语,现在我把它转赠于读者。且随马钧、李万华行走郊野,流连万象沉吟视听,感受啄木之鸟再次剥啄有声,做出一次珍贵的美的巡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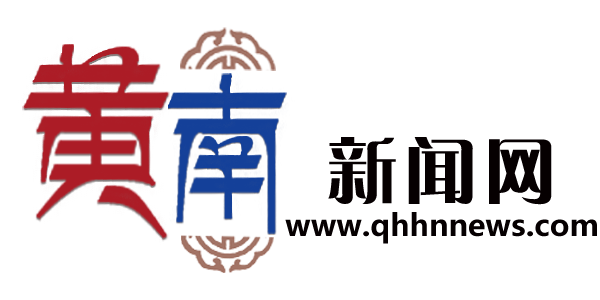

 青公网安备 63232102000018号
青公网安备 6323210200001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