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可可西里是一片荒原,它却是孕育生命的摇篮;
有人说,可可西里是生命禁区,它却是野生动物的栖息乐园;
有人说,可可西里是无人区,却有一群人坚守在这里;
……
8月15日,西然永平望着院子里的小藏羚羊,恋恋不舍地离开索南达杰保护站,前往格尔木市。临行前,西然永平再三叮嘱轮班值守的同事,“一天要喂4次奶,平日里多观察小羊粪便,晚上别睡太死。”
回到格尔木市后,每天睁眼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向保护站值守生态管护员询问小藏羚羊的情况。
让西然永平记挂的藏羚羊有5只,这5只小藏羚羊是7月13日从卓乃湖救助回来的,当时只有十几天大小,照顾小羊的“生活起居”成为了西然永平最上心的事儿。
“每天喂四次奶,8时30分、12时、16时30分、20时30分各一次,每次的量不能太多。喂奶前的准备工作非常细致,先要将袋装牛奶倒入水壶,加入适量的水,放在炉子上加热,等到牛奶沸腾后,放在屋外晾温。随后,把所有奶瓶放在铝锅中烧煮,等到水沸腾后,再将奶瓶取出晾干。”西然永平解释,牛奶加水是为了防止小羊拉肚子,沸水煮奶瓶是为了消毒。
西然永平说,照顾藏羚羊宝宝就像是在照顾自己的孩子,有时候,深更半夜还要去看两眼,就怕出现意外,西然永平将自己的这种行为称为“被迫害妄想症”。
西然永平所在的索南达杰保护站是可可西里最早设立的保护站,以环保卫士杰桑·索南达杰的名字命名,既是对先驱的怀念,更是遗志的传承。索南达杰保护站是可可西里藏羚羊救助中心,每年藏羚羊在卓乃湖、太阳湖等地集中产仔,巡山队员发现和羊群走散的藏羚羊幼仔后,会把它们带回保护站救助喂养,这里也被称为“藏羚羊幼儿园”,保护站生态管护员充当了“羊爸”“羊妈”的角色。
2002年至今,索南达杰保护站已有50多只小羊迎接新生,重回自然。
西然永平家住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是西南交通大学生物工程专业毕业的大学生,他原本可以有更多更优的选择,但他却留在了可可西里。
“谁说大学生就不能当一名生态管护员,可可西里是宝贵的遗产,总得要有人来守护吧!”面对疑问,西然永平坦然说,来可可西里之前,他对这里的了解并不多,仅仅是通过网络上的新闻,来了之后却喜欢上了这里。
其实,这不仅仅是西然永平的感受。可可西里仿佛能让人着迷,2016年4月,记者第一次进入可可西里腹地,整个行程将近10天。当时是跟随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工作组进入可可西里,有幸到达了区域内大部分的湖泊高山,那时候可可西里给记者的感受是荒凉,并不理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前赴后继守望可可西里。
当时带工作组进入可可西里的向导是索南达杰保护站的赵新录、龙周才加、郭雪虎三人。在太阳湖畔住宿的那一晚,帐篷内闲聊时,郭雪虎的一句话让记者记忆犹新:“可可西里的宁静是流血与牺牲换来的,为了保护藏羚羊,已经有前辈牺牲,英魂长眠太阳湖畔,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微不足道。”那天晚上,望着帐篷不远处杰桑·索南达杰的墓碑,看着满天璀璨繁星,心想也许有一颗星星正是索南达杰,他依然守望这片大地,未曾离去。
从可可西里回来之后,记者就迫不及待查阅与可可西里相关的资料,翻阅相关书籍,了解可可西里这片荒野,试图探寻一群人坚守一片荒野的意义,这也萌发了想再次走进可可西里的念头。
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这些年,每年会有一两次机会到可可西里采访,从昆仑山口到唐古拉山镇之间的边缘地带行走,有时候也会稍微深入一些。随着阅历的增加,渐渐认识到这群人坚守与守望的意义:他们不仅仅是藏羚羊和可可西里的守护者,他们真正守望的是人类心灵的归途。
当初,郭雪虎只是索南达杰保护站一名普通的生态管护员,如今的他已经成长为卓乃湖保护站副站长。记者与郭雪虎算是老朋友,一方面是相识时间长,另一方面可能是“同行”的缘故,每次采访会吐露一些真心话。
“2009年冬天的一次进山巡护,让我终生难忘,那天,我们的车辆陷入湖中导致油箱进水,车辆拖出来后,我们点了一堆火取暖,谁料火星引燃了身上的油水混合物。”郭雪虎说,当时火苗顺着他的裤腿直往上蹿,队友尼玛扎西抓起一床棉被瞬间扑盖在他的身上,火才算灭了。
郭雪虎家住玉树州称多县,早些年,他在玉树州广播电视台工作。2006年,郭雪虎辞职,毅然决然远赴可可西里,“当时听说可可西里招募巡山队员,我就辞职报了名。做这个选择时,很多人不理解,我的理由很简单,索南达杰是我的偶像。”
可可西里卓乃湖保护站属于季节性保护站,每年藏羚羊迁徙产仔时,郭雪虎都会和同事坚守在这里,一待就是几个月,但郭雪虎并不觉得这样的日子枯燥,“每天见证新生命诞生,看着它们活蹦乱跳,这就是我们坚守在这里的最大乐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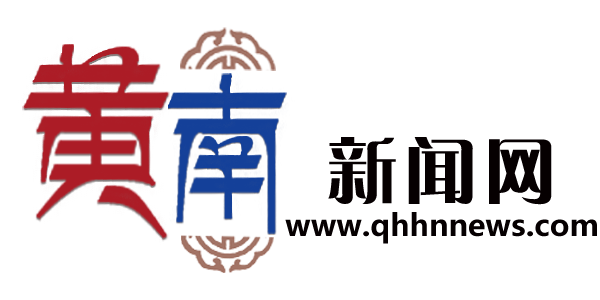

 青公网安备 63232102000018号
青公网安备 6323210200001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