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青海作家李万华是青海高原上的行走者,亦是静观者。行时群山排闼、花鸟相随,静时云卷云舒、江河入目……青藏高原上的风物在她笔下不仅厚重而又温暖,还流淌着新鲜而又明亮的生命力。
《群山奔涌》是李万华书写青藏高原风物的一部散文自选集,她以景入情,以情及物,用细腻的笔触,温润的文字,写出了青藏高原自然的宏阔壮美与生命的蓬勃绚丽。本期“江河源”副刊“特别关注”栏目特推出专版,刊发《群山奔涌》一书的序、后记、相关短评以及部分文章,敬请关注。

李万华,1972年生于青海。1990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出版散文集《金色河谷》《西风消息》《丙申年》《山鸟暮过庭》《山色里》等。作品曾获第十八届百花文学奖散文奖、第二届青海文学奖、青海省政府第七届、第八届文学艺术奖。
名家推荐语
李万华《群山奔涌》,是青藏高原一位女儿的凝视:反射蓝光的积雪,露珠似的山野花朵,从青稞芒里涌出的阳光,金色闪烁的寺……用美好文字描绘的这一幅幅凝视图景,安静或热烈呈现的,是作家的深情之心,是她对世界、对这片独特家园的爱和颂歌。
——无锡市作家协会主席、散文家、诗人黑陶
群山奔涌,宇宙翻腾。极具异质性的文字,浇灌15年河湟时光。每一秒都是秘密的宝石,布满了苔藓的宝石,构成了一个执着而清凉的文学星球。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作家庞余亮
李万华《群山奔涌》以青藏高原为背景,极具地域特色,回旋自如,浑然天成,毫无雕琢痕迹。既有博物学的严谨,又有文学的细腻。读之能从中获得一种沉静、深邃的品质,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散文佳品。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作家江子
李万华书写了大量的乡村名物、乡村物事和乡村风习,同时又融入了生态文学里对自然的书写(主要写动植物),同时也植入自己大量的生命记忆,隐隐刻录出一位散文家的心灵史。这种书写上的跨文体或者说在多种文体里的闪转腾挪,或对多种文体的兼收并蓄,无疑是对其写作所具有的杂糅特性的再度拓展。
——青海作家、评论家马钧
风从青海来
——《群山奔涌》序
□存 朴
我与李万华素未谋面,有限的信息交流源自阅读。起初,在博客读到其作品,如同开启一段阅读序曲,是一些短章或片段,“我仿佛是个,山野的王。我想着或许,果真,我在那些幽僻的地方,做过王。我将手脚散开来,搭着泥土,搭着草色,搭着蜂蝶,并且,搭着花朵的脸颊。”(《世界并非只由一种看法统治》)。“我在这样的阳光里静坐,听到些热烈的声息,在寂静中喧响。我听出它们最先产生于泥土深处,如同一粒种子的萌生,在幽暗中做些左右冲撞,然后沿着叶脉和松针弹射,并汇集些他物的响动,溪流、山风、鸡鸣、犬吠、牛羊哞叫。”(《这个世界还有更乱的人》)。这些文字,最平常的词语与句式,却产生独特的效果。沉思的品格,主观内省的精神底蕴,假设或想象的力度,隐隐可见其现代性写作的努力方向。读之,仿佛遇见一位前世的熟人,相知如故。
一晃十余年。
好多年,有两位“李万华”在视野中不断交替出现。一位是以“天風”的名字出现在日常里,偶尔以通讯工具交谈,话不多,寥寥数语,质朴,低调,有教养。另一位是以“李万华”的名字,在作品集、期刊杂志和微信公众号呈现。“天風”给我的印象是模糊甚至有点神秘的,我以为那是一位生活在青藏高原深处的男孩,偏于凝思,个性诚朴。这种印象维持了好久,我的阅读因而不断处于猜测中,如同她擅长的写作的假设。直到《金色河谷》《西风消息》的出现,我的一些猜测才落到实处。如果《金色河谷》中的行文面目安静、明朗,略带热情,视线偏于外向又暗伏着向上生长的力量,《西风消息》的气息,则像一位看尽沧桑的中年女性,同样安静的表达中,万念释然如一,如同修行之后获得“解脱法门”的慧者。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她的作品中,一是散见于期刊的散文《西风消息》,一是她获得第十八届百花文学奖散文奖的《丙申年》,两篇作品,都有仿若“慈航普渡”的读感。而倘若了解李万华本人所经历过的时间磨砺,自会明白,她的人与文,如此契合,如此莫逆于心。
迄今没到过青海,青藏高原之于我,有着土耳其电影《秋天》的风景底色和塔玛拉·科特夫斯卡导演的纪录片《蜂蜜之地》的人文想象。青海省的轮廓像一只猫科动物,静静地蹲伏在西部辽阔的版图上,图片的安静假象下,人文历史远溯秦汉唐宋,各民族宗教信仰由来已久,长江、黄河、澜沧江三大河流在此同源,青海的“花儿”就像《诗经》中的“风”,祁连山上,自然万象斑斓绚丽……这是一片神祇照临的土地,贫寒又丰饶,壮阔又灵秀。从出生到成长,从儿时到中年,绚烂归于平实,李万华像蛰居在山野清风中的古隐者,喜欢独自去旷野走走,吹吹河谷的风,听听鸟声啁啾,在黄昏观察一株青杨树的季节嬗变,在雪地之上看苍茫大地,一些大地深处的“消息”,梦境,时间,现代人的困惑与寻找,都在文字间扑面而来。
收录在这部散文集中的篇章,从《花鸟册》《山水册》到《杂画册》,貌似自然文学写作的外套,内里却珍藏着作者倾心浇灌的精神骨血,通过个体身心在自然怀抱中的“安放”与“对视”,探究人的“存在与时间”。这里,涉及到人的认知。认识自然难,认识同类也难,最难的,还是自我的认知。“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的座右铭,道出自我认知的困境与重要性。中国古代诸子和西方哲学语言,都在关乎“人之存在与认知”的精神路途奔走。本书中,作者笔下的那些花草,头花杜鹃、山桃、龙胆、马先蒿、香薷、披碱草、补血草开了又谢,谢了还开;青杨树的叶子绿了又落,落了又长;那些晚来风急时分或晓起薄雾中飞来飞去、鸣声自由的高原上的文须鸟、伯劳、松鸦、云雀、百灵,有着神灵度牒过的天籁之音;那金色河谷的一抹云霞、祁连山上的风雪、黄河岸边的芦苇、柳湾旧址的陶片、刚察的油菜花地,以及牧羊人的憨朴、西部村庄的记忆点滴、秋日与冬夜……就在年年月月的精神探究下,像群山奔涌一样,气势辽远而高峻,又像打乱了记忆与现实秩序的墨色,氤氲于纸面。有《论语》曾子“咏而归”的理想,有老子、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道德自律,有佛家“众生平等”的善良、谦卑与慈爱。在类似这样的精神寄养和自我认知里,解衣般礴,奔走之躯与想象之笔相互映照,李万华维护着散文写作的尊严。
阅读过程中,我的体验是不能沦陷于作品“及物性”带来的阅读假象,在高原自然地理风物的语言中“走失”。如果你把这部书看作仅是描摹自然万物、风土人情,也许你只是进行了一次纸上旅行,“走马观花”一般轻易。如果你沉下心来,跟随作品的“呼吸”,像作者一样观照自我,也许你将精神同频地“如沐春风”。相信你的眼力。阅读者的高端眼力,让写作者与阅读者收获到双重的体面,抑或教益;就像本书中青杨树的一片叶子,春生秋落,亦是教诲。
桃儿七

桃儿七 张胜邦 摄
□李万华
最初知道有种植物叫桃儿七是在读古岳先生的《谁为人类忏悔》一书时。记得这个名字与其他几种植物并列一起,就是说它们生长在同一个地方。那几种植物我熟悉,独桃儿七陌生。好奇之余查资料,书中的桃儿七出乎我的想象,它更如一种热带植物:花大如莲,樱花粉,花瓣六,叶如大黄,深裂,花绽放时叶子反折,果实如桃,青涩时翠绿,一旦成熟则呈橘红色。
翻寻记忆,实在没有桃儿七的影踪。对我而言,高原上的桃儿七更像植物界的神秘人,有某种无法言说的魅力,魔笛一样将人诱惑。
2021年立秋日,午后时分,在北山国家公园浪士当沟,循涧水而行,往山坳深处走。时节虽已立秋,天地仍是夏日模样,树木葱郁,掠过的风携带草药芬芳。河谷多白桦,山坡阳面多为柏树,阴面多是青海云杉。白桦林中东方草莓已经熟透,赤豆大小,色深红。没人采摘,草莓自己一点点失去水分,准备成为草莓干。摘几枚来尝,原始的酸甜。防风还在开花,它的花期可长达一个夏季,几株橐吾举起松花黄的花穗,玲玲香青的白有点毛茸茸的可爱,偶尔一朵甘青老鹳草,它是我熟悉的花朵。金露梅、银露梅、红花岩生忍冬、甘青瑞香等灌木的花已谢去。涧水喧哗,乱石矗立水中。蹲在水边洗手,水清冷,澄碧,撩水花时稍稍发愣,想起童年水边嬉戏的情景,却又瞬间回过神来,昔日终究不再,回忆徒增惘然。
愈往山坳深处,景色愈幽寂,偶尔一两声鸟鸣,不见鸟的翅膀。小路崎岖,拐个弯,忽然一处桃源:一面山坡用木栅栏围起,栏内两三户人家,早年土木结构的屋子,木柴和牛粪堆在一边,割来的青草晾晒在木架上。坡上几株大树,树冠如穹庐,树龄约在百年以上,仿佛柯罗画作里的树木。树下青草茂密,阳光照在草穗子上,一片浅紫波动,看不清楚的蓝色花朵在树阴里。不闻鸡声人语,一只羊羔站在柏树下,一对大鹅摇晃身躯来回走动,一畦土豆花还未谢去。想去人家屋下看看,发现栅栏门用铁锁锁住。云杉枝挂在木栅栏上,几枚松塔如艺术品正在展出。
转身时见到栏内一株植物,叶柄自乱草中高高挺起,六片大叶子撑开,状如手掌,叶缘粗锯齿,不见绒毛,叶柄间两枚手雷似的果子垂下,果皮光滑细腻,色如翡翠。果子陌生,不知是浆果还是核果,叶子有些熟悉,一时恍惚,想不起以前到底见过没有。
栅栏挡住,不能靠前,只远远拍了照片,想找认识的人问问。
山坳深处,红桦树渐渐取代白桦。红桦姿态各异,古铜色树皮层层裂开,似褴褛衣衫。树皮易撕下,捏在手里,薄薄一片,脆裂,抖动有声,如果手中有笔,能画幅图案出来。遇一株矮小红桦树,有人恶作剧,将大部分树皮撕掉,剩光溜溜火腿肠似的一截树干。陇蜀杜鹃出现在水畔,又有几株小叶杨。小叶杨显然已经生长多年,树干粗直,一人勉强合抱。有一株小叶杨只剩半截躯干,横斜在乱草翠微里。
立秋之日,又时近傍晚,气温迅速降低,风从后背透进,沿经脉乱窜。原本还想走一程,一直走到水尽处,但寒气迫使,只能返回。
惦念那一株不认识却又似乎熟悉的植物,回家对比照片再查资料,原来是桃儿七,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看图片上桃儿七花开,想到王维的“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一时有种与神仙擦肩而过的遗憾,只后悔当时没翻越栅栏入内,近距离去捏捏叶片,嗅闻一下它的果实气息。
《本草纲目拾遗》记载桃儿七,称它为八角连:识得八角连,可与蛇共眠。又说:八角盘,即鬼臼,今人所谓独角连是也。
伯 劳
□李万华
棕背伯劳站在珍珠梅高出的一枝上,不停歇地聒噪,仿佛南方的蝉。有一次,在苏州山塘街的水边,我听到一种蝉叫,声音异乎寻常地大,以为那是一只鸟。跑前跑后去找,没见到,朋友解释那是一种不寻常的蝉。不寻常的蝉,应该有某种鸟大,起码跟麻雀差不多,才配得起那么大的声音,我因此记住了苏州那种未曾碰面的蝉。蝉鸣是因为腹部有鼓膜,声音再大,持续时间再长,也感觉不到费力。棕背伯劳一直叫,音域窄,发音频率高,天光下,张开的小嘴巴来不及闭合。我仰头看几分钟,替它憋一股气,喘不过来,便坐在石头上大口呼吸。
郝懿行形容伯劳,说“其飞纵纵,其鸣鵙鵙”,鵙鵙,容易理解,伯劳的叫声。古人称伯劳为鵙,自然以声得名。但鵙这个名字不顺口,东飞鵙西飞燕,不如东飞伯劳西飞燕好听。其飞纵纵,理解起来有些麻烦。伯劳非椋鸟非麻雀,不喜欢拉帮结派,自然不会鸟飞千白点,日没半轮红,至于飞得快、猛、准,请问哪只鸟不是有方向而快速地飞。伯劳“句句句”地叫,有人说其叫声充满不快之感,恶鸟的名声,此乃原因之一。又有传说,认为伯劳是周宣王时大臣尹吉甫的孝子伯奇魂魄所化。尹吉甫听信继室谗言,误杀前妻之子伯奇,后悟,哀痛不已,一次外出,见一只从未见过的鸟站在树枝上悲鸣不已,尹吉甫心动,认为它可能是伯奇所化,于是说:是吾子,栖吾舆;非吾子,飞勿居。那鸟果然飞来停在他的车上,跟回家。鸟为魂魄所化,民间便认为“伯奇所鸣之家,必有尸”,认为不详。至于七月鸣鵙,说伯劳阴历五月开始叫,阴历五月阴气始动,是为“贼害”。伯劳因此成为“贼害之鸟”的说法,感觉更为不妥,五月开始叫的鸟多了去,难不成都是恶鸟。
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从一只小小伯劳鸟的身上,就能看出人的胡搅蛮缠。好在后来曹植为其恢复名声,伯劳若知,当感恩才是。
不过伯劳确有一种看起来比较邪恶的技能。伯劳喜欢吃昆虫、蛇蛙之类,它抓到蛇抓到老鼠,不会活吞,不会摔到地面,而是先戳到树枝上,一点点,血淋淋地将其撕扯。有时受惊吓飞走,尸体扔在原地,被风干。若来年树枝重新发芽开花,尸体还挂在那里,看上去颇为诡异。“鵙鸣其上,蛇盘不动,”这并不真实。事实是,伯劳逮了蛇,将其钉在荆棘上,使其不动。
中国花鸟画里的鸟,要么是仙鹤喜鹊之类预示祥瑞,要么是尾羽修长的孔雀寿带之类,要么是雉鸡鸳鸯色彩艳丽,要么是鹰鹫翠鸟戴胜之类某部位夸大突出。平凡的鸟自然有,麻雀燕子,大鹅野鸭,它们一到画中,便会以某种审美意向取悦于人。归根究底,生活与艺术始终不是一回事。宋之后,伯劳也渐渐出现在这样的画作中。看画上的伯劳,和树枝上的伯劳不一样。艺术作品里的伯劳,与意境结合在一起,是意境的一部分,如果剥离了意境,它便是孤单的,不完整。树枝上的伯劳,光着膀子露出胸,原生态,珍珠梅换做新疆杨,午后换做日暮,它还是它。它的背景反过来以它为背景,离开它,便显得僵硬。不过不管是哪里的伯劳,看上去,与邪恶没有任何关系。如果非要说有,也不过是目光更凌厉些,嘴巴有点像鹰隼,爪子强健,脚趾有利钩。
也许是午后过于安宁,伯劳无波动的聒噪让夏天更显慵懒。夏天就应该这样,风早已扬长而去,阳光棉袄一样堆在地上,蜻蜓们一声不出,小蝇子在空中集体巡游,暴马丁香的花已谢,菵草结出淡黄色颖果,一条有鳞的小鱼跃出水面,另一条睡在水面上。时间愈来愈远,事物因而变得模糊,人们都在昏昏欲睡,记忆里的身影越来越单薄,伯劳就在梦境边缘,扯着嗓门叫啊叫。
《群山奔涌》后记
□李万华
选在这本书里的文字,最早的篇章写于2007年左右,如《金色河谷》,最晚的,写于前几个月,如《群山奔涌》,之间将近十五年。十五年时间,一个人的身体,对事物的看法,对环境的反应都会发生许多变化。身体逐渐衰老,对事物的看法由简单到复杂,复回归简单,对人与物开始宽容,这个过程说不上好,但也说不上不好,它只是一个个体自然而然的规律变化,没有多少“自己决定”的成分在。文字不一样。文字没有一个由繁复至简洁,或者由朴素至绚烂的固定轨道存在,它大多随个人喜好,或者性情而变化。不过大致上,文字会随着年龄的增大而逐渐平实,所谓删繁就简三秋树。我自然也因循了这一条。
个体容易对自己的过去释然,这大部分归功于时间的冲淡,记忆力的衰退,以及拿过去无可奈何的无能为力。可是作为一个写作者,很难对自己的文字持如此态度。过去认为天花乱坠的,现在看大多飘渺不知何为;过去认为寓意隽永的,现在看大多华而不实;过去认为掏心掏肺的,现在看不过是小儿唏嘘……十五年后,要耐着性子重读自己以前的文字,是一件艰难的事。因为不想容忍,恨不得逐字逐句来一番大修改。但每每动手前,又按捺住自己:过去的自己都放过了,何必为难过去的文字。
一个认真对待写作的人,许多事可以粗糙,可以忽略,可以不求完美,惟独对文字要求高。所以无论十五年前,还是十五年后,无论风格、题材或者写作习惯如何变化,这期间每一粒出现在纸上的字都是郑重的,是老实的,没有油腔滑调,没有故弄玄虚,说到底,每一粒字都是我曾经真实的一部分。
如此,我便承认过去的文字就是过去的自己,我释然过去,也便释然了过去的文字。
感谢马钧先生。
感谢存朴兄作序。
感谢使本书得以出版的师友。
感谢您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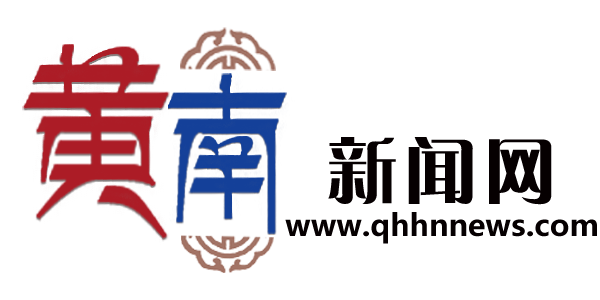

 青公网安备 63232102000018号
青公网安备 6323210200001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