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三意社为西宁市民送上了一场秦腔盛宴。(西宁市文化馆供图)
2023年的七八月之交,西安三意社来青海演出。演出地点是西宁市中心广场的百姓大舞台。每天早晚各一场戏,一共演了十场戏。十场戏场场满座。每次,戏还没有开场,台下就已坐得满满的。座位的后边,还有很多站着的观众,一场戏短则两个小时,长则三个多小时,从头到尾地站着,足见看戏者的真心诚意。那些日子,青海的戏迷们喜形于色,奔走相告,呼朋唤友,眼里看的,嘴上说的,全都是戏。我用“秦腔盛典、戏迷节日”八个字来概括其盛况,想来并不为过。
我在抖音上看过几场戏,又去演出现场看了侯红琴主演的《火焰驹》和杨升娟主演的《周仁回府》。侯红琴是西安三意社的台柱子。她的声音有天分也有训练,达到了一个纯熟而又自如的境界。她的演唱委婉缠绵,韵味悠长,颇具大家风范。她的念白字正腔圆,抑扬有度,表演规范而又洒脱,总能恰当地表达出剧中人的感情。杨升娟深得秦腔大家李爱琴的真传,是秦腔生角的后起之秀。她的唱腔流畅妥帖,感情爆发时,声如裂帛,高亢入云;需要低回婉转的地方,又能把声音压下来,唱得缠绵入骨,声声关情。特别是在“悔路”和“哭墓”等几个核心唱段中,杨升娟的演唱可谓揪心裂肠,从心所欲,一字一句,就像喷出来似的,把个有情有义、一诺千金的周仁刻画得入木三分。
台下的观众,以他们神态各异的表达,回应着台上的演出:有的伸长脖子,一眼不眨地盯着舞台;有的摇头晃脑地跟着演员唱;有的发自衷心地啧啧赞叹:“好把式是哩”;有的则高叫:“好!好!” “绝了!绝了”。来的人中,中老年观众固然居多,但年轻人我看也不少。他们中间,有陪着家中老人来看戏的,也有出于喜爱而来过戏瘾的。
中国有数百种戏曲,秦腔的曝光率和存在感算不上最高,但若论感染力和铁杆拥趸数,却少有出其右者。无论是在陕西还是甘肃,我都见识过,一场演出,台下观众有数万人之多,人山人海,乌泱泱一片。四边的人往里挤,里边的人往外扛,后边的人为避开视线的遮挡,有的站在拖拉机上,有的把孩子架在脖子上,有的爬到树上,一个树杈一个人。那种欢欣、热烈、盛大的场面,实在让人震撼,让人难忘。有时,戏正演着,忽然下起了大雨,但台下的观众却纹丝不动。看那样子,只要不是天上下刀子,他们是不会轻易撤离的。
说起一些西北人对秦腔的痴迷,也着实叫人错愕。我大学毕业以后,被分配到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的一个部队农场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封闭的环境,繁重的体力劳动,使人不由得产生一种自我宣泄的欲望。而宣泄的方式之一,就是吼秦腔。恰好,学兵连里有一个陕西财经学院毕业的同学会拉板胡。在他的带动下,我们几个来自不同高校的西北籍学生,得空就会在地窝子旁边的小操场上吼一阵秦腔。一天,一个同学正兴致勃勃地唱着《辕门斩子》中杨延景的唱段,另一位来自南方的同学却不以为然地说了一句:“歇斯底里!”唱戏的同学闻之大怒,他冲到那位江南秀士面前,怒目圆睁地说:“什么歇斯底里!这叫响遏行云!这叫振聋发聩!你知道不知道,鲁迅先生还专门到西安易俗社去看秦腔呢!”那天,要不是众人合力劝解,这位容不得别人抹黑秦腔的关中楞娃,说不定就会拔拳相向呢。这是西北人酷爱秦腔的例证之一。还有一例:我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工作的时候,曾经遇到过一位堪称秦腔迷的州人民政府副州长。20世纪80年代初,我跟随这位领导到州属各县开展调查研究。那个年月时兴有线广播,一到早晨、中午和晚上的广播时间,覆盖县城的大喇叭就响了。除了播新闻,还会播些音乐和京剧、秦腔、豫剧等戏曲唱段。调研期间,有那么几个中午,我们已经坐在县招待所的食堂吃饭了,街上的大喇叭骤然唱起了秦腔。一听到那激越、苍凉的唱腔,州长便放下饭碗,跑到房子外面听戏去了。我们让他先吃饭,他却连连摆手说:“陈仁义的《下河东》,来劲!你们先吃,让我把这段戏听完。”陈仁义先生哪里知道有人因欣赏他的演唱而忘了吃饭,还在广播中没完没了地唱着。州长怕耽误大家吃饭,就走回来给碗里搛了点菜,拿了个馒头又出去了。他圪蹴在房檐底下边吃边听,俨然一副关中老农的做派。
我的秦腔癖也许还达不到这位领导的高度和深度,但自感秦腔已经化作基因,融进了我的血液。我出生在一个有着浓厚秦腔氛围的农民家庭,父亲是村上秦腔自乐班的骨干成员,戏唱得好,板胡也拉得好。别看他只上过两年学,识字不多,但却能把诸如《三滴血》《游西湖》《五典坡》《铡美案》《法门寺》《玉堂春》等秦腔剧本一本一本地背诵下来,尽管这些剧本常常是之乎者也的字眼。每逢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唱戏(陕西人把这种不登台表演的唱戏称为“喧荒”),父亲就会带上我。他和他的伙伴们投入地、忘情地唱着,我待在一边静静地、痴痴地听着。至今,我仍然怀念那些在丝竹管弦之声中度过的日子,那其实就是我最早接受的文化熏陶和文学启蒙。我特别喜欢自乐班那种不择场地、不上舞台、不收取报酬也不求取悦他人的自我表演,喜欢那种随心所欲、无拘无束的自我流露和自我释放。而正是在这种绝少功利目的的极度放松的心态之中,关中农民那种质朴、那种真诚、那种简单、那种知足常乐的生命状态,才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耳濡既久,我也便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几个唱段。虽然唱得不怎么好,但熟悉板路,知道胡琴拉到什么地方该唱,什么地方该停。如果某个唱家不在,临时顶岗唱几句,也还不至于十分蹩脚。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遇到一个特别喜欢秦腔且又爱拉板胡的班主任老师,他正发愁没人与自己合作,一听说我能唱秦腔,自然喜不自胜。他找到我说,每天吃过晚饭以后,只要你没别的事儿,就到我的宿舍来唱一阵儿,然后回去自习。我没有理由拒绝他。于是,在上初中以前的两年时间里(星期天和假期除外),我于课业学习之外,又给自己附加了一个“天天唱”的课目。上大学以后,我所在的兰州大学工会牵头组建了一个秦腔业余剧团,排演了马建翎先生创作的秦腔现代剧《血泪仇》,我饰演剧中人物王东才。除在学校演出外,我们还在兰州市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做过巡演。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班乃至我们系的同学,见了面就叫我王东才。
人的兴趣爱好是很难改变的。我到青海以后,依然故我地爱着秦腔。粉丝这个词,好像是近十来年才出现的新词,但粉丝现象却早已有之。对老一辈的秦腔大家和这些年涌现的众多秦腔名角来说,我从来都是他们的粉丝。对他们一向怀有“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崇拜心理。但凡西宁有秦腔演出,我一般都不会错过,就连互助、大通等地农民演出的秦腔剧,我也兴致盎然地去看过几场。我积有30多盘秦腔磁带和CD光盘,其中,有些是自己买的,有些是别人帮我翻录、选录的。闲暇之时,泡一杯热茶,放一段秦腔,那种惬意,那种自得,那种幸福,真是难以用语言形容!
有时候,连我自己都觉得奇怪,时代已经进入21世纪,影视综艺、短视频游戏、流行歌曲、广场舞、抖音、快手等文化休闲方式沸反盈天,随处可见。鲁迅先生称之为“古调”的秦腔,不仅还能”独弹”,而且还拥有如此蓬勃的活力,还能得到这么多人的喜爱。个中原因,实在值得深思和研究。作家贾平凹在他的散文名作《秦腔》一文中,对这个问题做了如下的回答:“秦川的地理构造与秦腔的旋律惟妙惟肖,秦腔又与西凤白酒、长线辣子、大叶卷烟、羊肉泡馍共为秦川人的五大生命要素,故而秦腔是秦川的天籁、地籁、人籁。”贾平凹的说法不无道理,但还不能完全服人,因为,喜欢秦腔、高唱秦腔的,并非秦川一地。许多青海人、甘肃人、宁夏人、新疆人对秦腔的痴迷程度,一点儿也不比陕西人逊色。三意社在西宁的演出尚未结束,下一站要去的甘肃甘谷、秦安、天水等地,人们已急不可耐地在抖音、快手上频频发问:三意社什么时候来啊?其翘首盼望的殷殷之情、急切之态,跃然屏上。
我的大学同学、已故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是个货真价实的秦腔迷,甘肃天水人。多年以前,他去新疆开会途经西宁,约我共进晚餐。席间,说起秦腔,他竟口若悬河,滔滔不绝。雷达半开玩笑地对我说:“贾平凹把秦腔说成是你们陕西人的专利,那是他‘陕西沙文主义’倾向的表现。秦腔之迷人,不在羊肉泡馍,不在长线辣子,关键在于‘苍凉’‘悲慨’两大特色上。”他还说,秦腔擅悲剧,不擅喜剧,擅伦理戏,悲欢离合的共情戏,不擅政治戏和理性戏。说这话的时候,雷达已带有三分酒意,但我却觉得他的这一番谈吐很有见地,非酒精上头者所能道也。他的观点既与古人说的“西北之音慷慨”一脉相承,也与我对秦腔和“花儿”的认识非常接近。“花儿”的优长,“花儿”的魅力,不也就在这“苍凉”“悲慨”四个字上吗?
大西北地区是一片壮美与苍凉并存的土地,也是古代的中原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的交汇之地。这片土地上承载过数不胜数的故事,兴衰荣辱、忠孝节义、悲欢离合、酸甜苦辣等世间百态在这里轮番上演。这里的历史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本身,就带有“苍凉悲慨”的韵味。秦腔也好,“花儿”也罢,不过是这“苍凉悲慨”的一种外化,是在大西北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人们的思维方式、情感方式、伦理方式的一种艺术化的呈现罢了。
“喝烧酒捧起个大老碗,吼一声秦腔震破天。祖祖辈辈吼了几千年,吼声里有血有泪,有苦也有甜……”因为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所以,我相信,作为中国戏曲中历史最为悠久的剧种,秦腔,还会一直吼下去,就像作家陈忠实所说的那样:“黄土在,秦人在,这腔儿便不会息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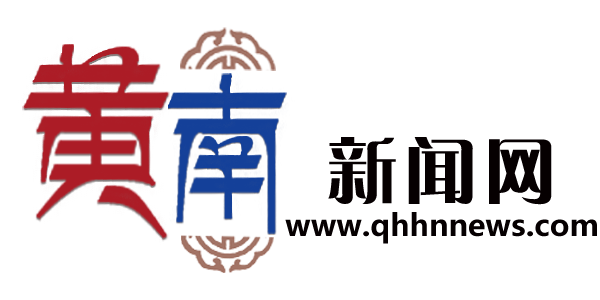

 青公网安备 63232102000018号
青公网安备 6323210200001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