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治沙,在扩展的绿色面前,当年肆虐的黄沙正在一步步退却。李春 摄
女性是黄沙头治沙的重要力量。 贵南县委宣传部供图
每年春雪还未消融,黄沙头的治沙行动就已展开。贵南县委宣传部供图
贵南县木格滩的黄沙曾经像一条势不可挡的河流,从西北方往黄沙头奔涌而来,让人叹息,让人绝望。如今,黄沙正在退却,翠绿从近到远、从无到有、从有到丰,从丰到秀,再到如今的千山堆绣、百川织锦,竟让人不知黄沙头何以名为“黄沙头”。
——题记
在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南县黄沙头,有一小截如坠落在广袤绿色里的黄沙带。曾多次听人感叹过贵南人治沙的不易,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来到曾经以黄沙而闻名的贵南县黄沙头,在一个小型的帐房超市里,听人讲让贵南县人民刻骨铭心的治沙精神。
他叫杭青旦增,是一位典型的藏族汉子,皮肤黝黑,身形偏胖,今年已经69岁了。此刻的他,白皙的光脚挑着一双很时尚的“狗屎拖鞋”,脚上皮肤的白和脸、手的黝黑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一边倒弄着一个酥油桶,一边给我说,治沙就要像做酥油一样,有耐心、能吃苦,要经得住失败,要不然它就会酸了、会坏了,成不了香甜可口的酥油。
杭青旦增用这句手到擒来的比喻打开了他27年的治沙生涯。
那是1996年的春天,杭青旦增在妹夫的带领下从贵德县罗汉堂村来黄沙头靠治沙挣钱。那时候沙漠在草原的流动速度让人瞠目结舌,吹一场风就会淹没400亩(1亩≈0.0667公顷)左右的草场。住在黄沙头附近的牧民,每年都在沙漠的逼迫下一步步退往大山深处,人和牛羊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大量牛羊因为常年缺草缺水,膘瘦体弱而熬不过高原的冬天。每到冬春两季,高原季风带着黄土沙子走村串户、张扬肆虐,让周围乡镇的住户苦不堪言。
就在那个时候,杭青旦增成了贵南县第一批治沙人。
“那时候日子很难,难得有时候都觉得熬不下去。”说完这话,杭青旦增很久都没有开口。他眼周的皱褶在那一瞬挤成一团,目光慢慢越过如厚重屏障的翠绿,望向更深处的天际。
“那时候,这周围没有一棵树,放眼望去一片昏黄,草原埋在沙子里,沙子流动在马路上,往沙漠里拉运树苗就成了最难的事。好不容易从其他地方拉来了树苗,一场场不期而至的风把沙子吹成沙丘,堆积得到处都是,车轮陷在沙里动不了,树苗只能由人来抬。黄沙头海拔高,路程远,本来人走在沙漠里就很难,抬着树苗走就更难。一脚下去,沙子淹到了脚踝处,用力一拔鞋子就掉了。有好多人习惯穿着靴子走,看上去沙子没靴子高,但走着走着,沙子就塞满了靴子,越走越沉,越走脚底越疼,走一阵就得脱下靴子抖干净,再穿上。往往一车树苗,四十多个人得抬一天,大家所有心思都放在了干活上,手、脚都没感觉到疼。在坐下休息时才发现,手心脚心全是泡,有些水泡都磨破了,沙子嵌到肉里,火烧火燎地疼。
“四月的贵南,早晚冷中午热,尤其快到正午的时候,沙子晒得发烫,沙地反射的光烤着露在外面的皮肤,脸和手干得像老杨树皮,一层层脱落。
“27年了,脸上、手上的皮肤一层一层脱下来,就成了现在这个黑黢黢的模样,怎么洗都洗不白。”杭青旦增自嘲地说。
“那时候,最缺的是水。沙漠一年年往前移,埋没了草山,堵塞了水源,没有水、没有草,人和牛羊就只能一次次往大山深处搬,水源地离我们很远,吃水、用水就很困难,十几天不洗脸、不洗手是常有的事。没有大型水罐车,我们把大水桶焊接在手扶拖拉机上,从十几公里外往这里拉水。有时候,去的时候晴空万里,突然一阵风吹来,路就被堵了,拉水车进不来,我们只能组织人力一桶一桶往帐房里提。等深一脚浅一脚到了帐房,水就剩了半桶。有些人提着水走着,脚下一崴,水都洒在沙地上,一下子就没了影子。
“那时候,最盼望的就是下雨,只要有黑云飘过,大家就拖出早早准备好的塑料布,七手八脚把塑料布拉开,四周稍微垫高一点,把雨水集在塑料布上,装在水桶当生活用水。也有人在下雨时会在沙地上挖个大坑用来储水,等水积得差不多了,就捞掉漂浮的干草枝、牛羊粪等杂物,也用来当生活用水。等所有的水桶都装满了,衣服裤子也湿透了,大家索性在大雨中脱掉衣服裤子,站在沙堆上,酣畅淋漓地用雨水洗一次澡,虽然冷,但快活。
“四月的雨天很冷,被窝潮湿阴冷。但大家还是盼着下雨,只要有水,人、牲畜、树木和草种都能饱饱喝一次水,树木成活率就高了,治沙的效果也会好点。”
当我问道:“吃饭时会不会吃到沙子?”杭青旦增一脸的皱褶笑成了朵朵菊花,他调侃道:“你没见我现在这么壮实吗,我身体里一半的重量可能都是沙子,我血管里流动的应该就是血和沙子的混合物。”
“那时候,我们有自己的厨房,早饭、午饭吃的都是自己做的馍馍,晚上再吃一顿面条。面粉装在袋子里,上面包了两三层塑料布。师傅在做馍馍面条前都会反复拍掉袋子上面的灰尘,做好的馍馍也会很仔细地装在塑料袋里,包裹得严严实实,再挂到树上,想着这样沙子就进不去。可是,到吃饭时还是会吃到一嘴一嘴的沙子,尤其是吃完面条,碗底就会有一层沙子,吓得我们连汤都不敢喝。
“沙子这个东西还真是奇怪,你包裹得再严实,它还是会钻进来,和你较劲、欺负你,你却拿它没办法。现在正好相反,我们治沙,每天一点一点用草方格去占沙漠的地盘,虽然会吹风、虽然有破坏,但它还是得乖乖受我们约束,拿我们没办法。”杭青旦增大笑着说。
一打开话匣子,杭青旦增的话就停不下来。
他说:“那时候在黄沙头睡觉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我们住的地方,方圆几公里都是沙漠,也不知天天都在吹的风是从哪来的,风从沙漠吹到沙漠,再吹到更远的沙漠。周围没有草和树的堵挡,沙子尘土满天飞,眼前每天都是昏昏黄黄的,耳边呼呼的风声就没断过。
“记得1996年4月的一个夜晚,我们几个工程负责人像往常一样,记录完一天的用工情况,扯了扯第二天要干的活后,就各自回了帐房。回去的时候,风像往常一样鼓满整片沙漠,吹起衣服下摆,有沙子打在脸上,麻酥酥的。我习惯性地抬起头看了看天,月亮周围没有昏黄的‘风圈’。就大步走进自己的帐房,脱了鞋和衣就睡着了。
“迷迷糊糊听到有人在大叫‘帐房吹走了!’还没来得及想一下到底发生了啥事,冷风一下子灌进帐房,我的账房也被连根拔了起来。没了堵挡,被褥、锅碗瓢盆、生活用具吹得到处跑,一眨眼就不见了踪影。周围有女人的哭喊声断断续续传来。一片昏黄中,我们大声询问着各自的情况,远处有一两个声音时断时续传来,时不时有模糊的身影跑过,去追被风吹走的东西。
“在零下几度的深夜里,我们紧紧抱着剩下不多的物品,瑟瑟发抖地苦捱着,期盼着,等风变小,等太阳升起。”
那一夜很长,杭青旦增和其他几百个治沙人,就像一株株刚刚生根发芽,随时都会被风连根拔起的沙蓬,不知道当下会遇到什么,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只有在狂风不停的寒夜,悄悄隐藏起身体里剩下不多的温暖,等着风停。
这种足以吹散所有希望的风,每年都会出其不意地来几次。它就像一个精于偷盗的惯犯,每次都会用流沙埋没很多刚刚发芽的树木,吹走一些才显绿的沙蓬和刺草,每次都会把治沙人用汗水和辛劳垒砌的信念和希望吹走一些,再吹走一些。然而,第二天早晨,大自然又若无其事、毫不吝啬地把阳光倾泻在沙漠里,用不断升高的温度为大家储存温暖,积累希望。
“再难也要种下去,不是吗?”杭青旦增眼中透着坚毅,“那时候参加治沙的不只是我们,还有很多省军区的干部、贵南县委县政府的干部,还有各乡镇的群众。那时候,好多群众由于常年放牧,家里连铁锨都没有,刚来的时候都是身子趴在沙漠里,用手刨坑种树,他们那么难都坚持下来了,更何况是我们这些专业治沙的。
“现在好了,你看,我们都快赶上现代化了。链轨、挖掘机、推土机,现在的设备越来越多,越来越先进,而且贵南县治沙造林已经二十多年了,也积累了很多的治沙经验,我们用链轨推平沙漠,用挖掘机建草方格、用推土机运树苗,在沙漠上修了很多明暗水渠,还用上了最先进的喷灌技术,在一些灌溉系统暂时到不了的地方,就用康明斯汽车拉水浇灌,植被成活率可高了。现在我们的治沙速度也在以曾经流沙的速度增长。相信过不了多久,你想来贵南看沙漠也没地方看了呢。”杭青旦增自信地说。
我顺着杭青旦增的目光望去,视线所及是一片翠绿。杭青旦增带着我去了一个专门看沙漠的高台,从这里向远处望去,一截沙滩如黄色丝带坠饰在广袤的绿毯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翠绿。“那就是我们现在治沙的地方,那些绿点是草方格和刚发芽的树木,到明年这时候,这些草方格就会和这里一样绿。”杭青旦增信心满满地说。
是的,我也相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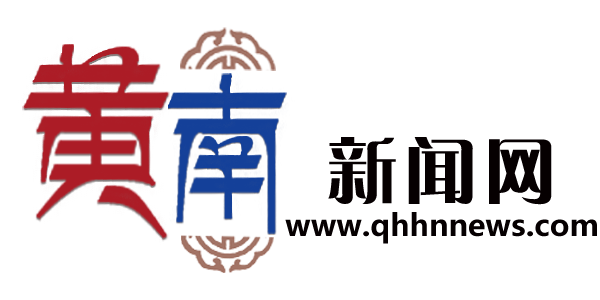

 青公网安备 63232102000018号
青公网安备 6323210200001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