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故乡物事的吟咏,长久以来使得多少诗人煞费苦心深耕其中而不能自拔,这种寻根情结无时不散发着诗性的光芒和蓬勃的生命力。诗人们追求思维方式和主体境界的高度融合,或直抒胸臆,或抚今追昔,或触目伤怀,随便拎出一首就能挤出或多或少的乡愁来。在诗人的笔下,熟悉的景象在脑海里升华,感性和想象力充分发挥,一草一木都被赋予灵性,给人以无限的遐想、深刻的思考和唯美的享受。如此,我想谈一下土族诗人东永学的诗歌,他的诗歌注重实质性内容又不囿于传统范式,属于近距离的乡土叙写,个性化特征明显,一字一句像是从泥土中剥离,世俗的华丽辞藻黯然退去,山野的纯净清爽扑面而来。
读东永学的诗歌,总能给人清新自然的感觉,一种既无那种刻意为之的矫揉造作,也无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故弄玄虚,看似清淡的叙述中不乏突兀的想象,率性而为是他诗歌的一贯特质。追求诗的意涵使得他更加理性地感知眼前的世界,将视觉里的万事万物进一步具象化,使原始的虚幻与现实的真切交融,再以简约的语言和真实的情感表达出来,达到惯性与张力的契合,从而形成他表达意象的独特风格。这种不落俗套的写作方式,体现在他的诗歌中,有回望故乡的愁思,也有恣肆江湖的快意。如在《祁连山》一首中,他写道:祁连山走到我家乡的时候/低了腰身,松柏爬上了肩膀/夏天的紫杜鹃是飘舞的腰带/让高原男人不再那么粗狂潦草。可以看出,不太在意韵律但并不影响诗歌的节奏,这段所展现的景象是巍峨雄奇的祁连山,从远古的洪荒中拔起,而当“我”发现它的时候,它已经与“我”为邻,视野渐渐收近,彼此的凝望中“我”也站成了山的高度。“松柏爬上了肩膀”是很富有哲理的叙述,这里不光是点明海拔问题,而是诠释各种生命赖以维系的自然法则。后面的两句则以如梦似幻的想象和形象贴切的比喻赋予山的灵魂,突出人与自然相互依存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期许。少年时跟着父亲走进祁连山/喊山是为了喊落松动的风化石/青年时登上有敖包的一座山顶/登高望远中寻找一朵托梦的鹰翅。这结尾的一段中,诗人的思绪进一步与自然亲近,着眼于事物发展的走向,如捡拾风化石一样寻找遗落的旧时光,而敖包上桑烟泛起,高空上鹰的羽毛滑落,情景交融中一种殷切的希望陡然滋生。又如在《铁青马》中,诗人写道:祁连山南北漠风劲吹/苍狼守着唐代的烽火台/红狐找到半截宋朝的断剑/铁青马从明代轮回到清代/从冷兵器时代到今天/草原风吹不出牛角号声/羌笛在那遥远的地方独奏。这个就有点狂野的意味了,说句玩笑话,不会玩穿越的诗人绝对玩不出超乎寻常的想象,只要敢想尽可以逸兴遄飞,当然我说的是个性发挥,不排除张弛有度。作为土族的一员,诗人自小在祁连山脚下长大,熟稔这里发生的一切变化,而当他重新审视这片土地时,金戈铁马的时代已经过去,从历史缝隙里走来的片段已不再囿于传统意义上的征战杀伐,这方土地多舛的命运与人类文明的更替紧密相连。镜头回到眼前,草原上的角声和羌笛声也已随风而逝,只有祁连山还是祁连山,亘古不变。诗人勾勒出的这个意境,看似虚幻,实则是宏阔背景下一个村庄前世今生的嬗变,除此无它。
不难看出,在东永学的许多诗歌里,故乡风物如影随形,这种挥之不去的乡土情结,成为他诗歌创作的原动力,而贯穿于其中的诗性思维无时不撩动他笔耕砚田的冲动,使他不得不一次次地回望故乡,走近故乡,让故乡的轮廓画满脑际,让故乡的一草一木触手可及。熟悉的民族风俗和生活中的细碎往事,无不成为他笔下的优美意境,一字一句富有质感。如在《家》中,他写道:碗底碰锅沿/祁连山上风和雪的碰撞/消融在一起/修补皲裂的门窗/感受一匹枣骝马的刚烈/骑手的幸福和荣耀/打造一所牡丹送香的庭院/见证双手刨扒的艰难。解读这首诗,大可不必将思绪放飞在大山的褶皱里,它指的就是我们所经历着的实实在在的生活。这其中,一个细小的碰撞也许会激起整个世界的震荡。强烈的画面感不时切换,夸张而富有节奏,锅碗相碰能搅动祁连山的风雪弥漫,扑打在破旧的门窗上,如同一匹桀骜不驯的烈马,而驯服这匹烈马需要优秀的骑手。而最终,矛盾得以消弭,一切回归宁静的生活。应当肯定,这段诗歌很富有哲理性和穿透力,有悸动过后的温情,给人以无限的遐想空间,进而感受蕴含在其中的意境之美。接下来诗人写道:许多日子里/你的任劳任怨是一支羽毛/白色的吉祥鸟的赠与/用光阴装订平凡人的幸福/琴棋书画是补丁/种下麦子供养肉体的饥荒/酒神住在一颗青稞里/满月的晚上和我们载歌载舞。经历阵痛后的山野和乡村终于迎来久违的惠风和畅,人的付出和自然的赐予相辅相成,时光往前赶便是凿饮耕食的人间,丰收的季节到来,四处歌舞升平。其中“酒神住在青稞里”这种拟人化的形象比喻,表达了人类对天地万物的敬畏之情,有粮食才有温饱,才有酒,才有精神层面的享受,这是递进的关系,也是辩证的过程,是灵魂的拷问和思想的升华。在《重阳》一诗中,同样,诗人聚焦于雪山大地,以一种虔诚的仪式烘托气氛,让大地散发出圣洁的光焰:致敬那些放风马的人/还有那些煨桑酒祭的人/这一天,山神肃穆/古老的仪式毕恭毕敬/顺着山脊前行/前方有白海螺的召唤。诚然,美好愿景的实现,大都肇始于行动之前的决定,出发前的动员也是必要的,追求的过程虽然艰难如同沿着山脊行走,但方向十分明确,那就是“白海螺”吹彻的地方。整个过程视角冲击明显,细节呼之欲出,投射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度默契和永恒定力。
东永学的诗歌,更多的是追求诗歌的价值取向。他往往将真实的生活场景置于艺术熏染的氛围中不断打磨,由此流露出的思想情感和意境之美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寂静的山野不带有一丝红尘的喧嚣,草坡青青像要流出绿色的汁液,坚硬的岩石如高山裸露的骨骼,还有弯曲的村巷,袅袅的炊烟,翻滚的麦浪,馥郁的花香,牛圈,马粪,牧歌,铁锨,犁铧……乡土气息,脚底带泥,所有的创作素材一齐涌入他的眼帘,成为他诗歌创作的不竭源泉。在《父亲节》一诗中,诗人写道:端一碗青稞酒/游牧时代的黑帐篷/木盆里金黄的酥油/银子的奶茶壶和酒壶/勤劳温婉的女主人/走在阿爸深情的吟唱里/引导阳光走向我的心里。这些景象很具体,或者说就是一幅灵动的生活画卷,土族的日常习俗,通过酒、黑帐篷、木盆、银壶等衬托出来,特色明显,而作为主角的父母才是其中的亮点。朴实勤劳的父母在完成一天的劳作之后,在黑帐篷里享受短暂的闲暇时光,歌声响起,往事如在眼前,乡愁还在路上。在《日记》一首中,他又写道:大雁向南飞去/秋天的落叶随风北上/此时,不适合抒情/更不能唱浪漫的歌谣/妹妹,秋天里的青稞/等着镰刀的痛惜与酣畅。这个就是秋天里的愁绪,大山深处的青稞才刚刚成熟,正是收割的季节,秋叶落,雁南飞,寒凉也紧跟着到来,这一番景象,似在感叹人生机缘的转瞬即逝,也似在揭示自然规律的不可逆转,而镰刀收获青稞的痛楚和幸福感,或许才是这首诗的精髓所在。在《卓玛》一诗中,他写道:卓玛姑娘是个名词/清纯如高原上十万海子/双眸秀澈,心思单纯/卓玛驻守在美丽的草原/卓玛是个动词/银鬃马驮负美丽的想象/马蹄翻滚,爱情飞扬/卓玛奔跑在小伙的心里。卓玛姑娘美丽善良热情大方舞姿曼妙,甚至还有点俏皮,很符合山野粗犷辽远的味道。诗人放下酒碗唱着情歌走向远方,卓玛扬起鞭子从后面追过去,欲嗔还羞。这一幕我们似曾相识,就在王洛宾的歌曲里,灵动的画面足以抚慰我们焦灼不安的心情。而实际上,诗人在这里采用了暗喻的手法,他的目光从未离开他念兹在兹的故乡,卓玛是一切美好事物的象征,是信仰和真诚的化身,是无处不在的大地的精灵,在山顶,在河谷,在密林,在草甸,在诗人追寻的意境里,在烟火升腾的人世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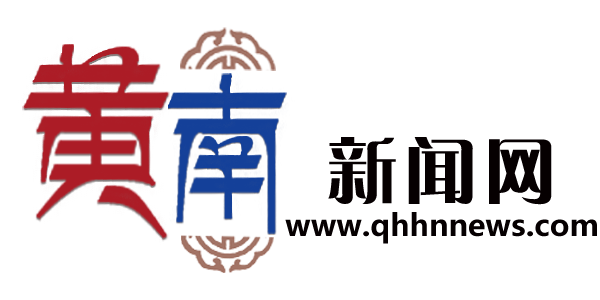

 青公网安备 63232102000018号
青公网安备 6323210200001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