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的春天,我十岁,建德哥十二岁,我俩整天钻在一间堆放生产队杂物的仓库里,兴致勃勃地捣鼓着一些五颜六色的社火道具。建德戴着一付面目狰狞的面具,煞有介事的掸一下长髯,唱:“我大哥上山为王,我二哥下山为强”(社火《杨林夺牌》)。我则舞弄着一根缀满铜钱的哨棒,来回敲打着那些能发出巨大声响的鼓、铙钹,从早到晚我们肆意搬弄着那些社火道具,没人来管我们,更没人来观看我们的蹩脚演出。
大人们似乎很忙,三三两两聚在村头巷道谈论着一些在我们看来十分神秘的事情,一个个表情严肃而又凝重,像秘密集结的地下党。窃窃私语了许久,终于在一个月圆的夜晚,父亲所在的第四生产小组的各家家长站在老孟叔家那间烟熏火燎的伙房里,开始商议如何分配村小组土地、农具、牲畜的事。土地、农具很快按数量、人口分定了,但到分牲畜的时候,大家都作难了,生产队解散成村小组后,给第四小组十三户六十四口人分了七头牛、四头驴、两匹马。现在按户再次一家一户进行分配,抓阄结束后,大家发现这种貌似十分公平的方法,却出了大问题,有些劳动力多的人家抓了好牲口,缺劳动力的人家,却抓了年老力衰且料口很重的老马。吵嚷了一个多星期后,父亲和几个村小组头头在忍痛割爱与人调换了牲口之后,分牲口的风波方渐渐平息下来。
自己种着自己的田,少了扯皮看样子。日子似乎与往常没有什么两样,庄稼照样浇水、拔草,但一些事情却在不动声色地变化着。首先,以往那些成片荒废的滩涂荒地在不觉间都被开拓整理成了农田,整个村庄从早到晚到处都弥漫着新鲜泥土的馨香;人人走路看上去都火烧火燎的,就连一向被村人认为最懒散的韩老八,不知从几时起也把紧靠自家麦田的一片石头滩愣是开垦成了一片平整的土豆地。至于村庄周围那些沟沟坎坎的犄角旮旯几乎在短短的一个春天里 ,都被规整成了一幅幅条条块块的几何图案,悉数栽上了柳树、白杨、榆树。以往需要忙半个多月的春种,现在不管是有牲畜的人家还是没有劳动力的人家,都在短短的一个星期之内全部完成了播种。放到往年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奇迹,恨的已退任的老队长咬着一根烟管逢人便骂:“这一帮贼骨头,往年为生产队干活,一年天气也没见你们这几天干下(ha)的活多”。但谁会在意他的话呢,这不是在为自家田里出力吗,再不是以往那个日上三竿,队长催促三四遍才磨磨蹭蹭上工的年月了,谁还会磨洋工呢。多流一滴汗水,就会多打一斤粮食哩。人人起早贪黑地忙碌着,四处给庄稼找地肥,原本一到夏天便臭气冲天的村厕,不知几时已被人连夜掏的干干净净,这在以往,就是队长给好多工分,有人才会哼哼着去干。
人不哄庄稼,庄稼也不哄人,当布谷鸟嘹亮的啼鸣声在濛濛春雨中越来越绵长时,禾苗儿便渐渐显现出少有的茁壮与厚重来,放眼望去绿油油的泛着光亮,株株开始分蘖扬花。每天天一亮都有人兴奋地在自家田头转悠,回来便笑不拢嘴地偷偷对家人说:“白石头干滩那片秃头地,你去问问徐家老爹,他种了五十年的庄稼几时见过今年这样的长势”。
日子随苦难而漫长,又因舒心而短暂。田黄一袋烟,不觉间便到了秋收的季节,每天,天还未亮,父亲便坐在院子里,喝着牛血一样的熬茶,就着三星晨露,开始把镰刀磨成一把凌厉的弯月,待晨曦微露,便把我们兄妹三人从被窝里撵起来,往每人手里塞一把小镰刀,赶着我们和他一起去割麦子。父亲说:“二八月,虎口抢粮的日子,绣姑娘都要下炕做饭,也该到你们出力的时间了”。
秋日的旷野秋高气爽,蛙鸣声此起彼伏,夜莺在歌颂秋日的丰硕与五彩斑斓。麦田方方正正像刚出炉的冒着热气的面包,麦秆齐刷刷的,挺直了腰板,像一排排等待检阅的仪仗队。镰刀搭在劲挺的麦秆上立即传递给人丰收的韧劲与殷实。一个麦捆三个头,俯身割麦子;起身抱麦子;再俯身捆好麦子……炙热的太阳悬挂在天边像被钉死了似的,永远也不知道下山,只剩下让人窒息的闷热和顺着下巴尖滴滴嗒嗒掉落在板地里的汗水。起早贪黑苦熬了一个多星期后,最后一镰庄稼终于被割倒打成捆了。手叉着腰望着满地的麦捆和四散逃窜的蚂蚱,一股横扫千军的成就感不由从心底油然而生。站在晨曦初露的田野,吮吸着旷野清新的空气,眼望着那一轮冉冉升起的朝阳,我隐隐感知一个全新的时代已经来临,而我在这一年里体会了许多,似乎也长大了许多。
那一年秋收,我们装满了家里所有能盛下粮食的口袋、水缸、坛坛罐罐,以及一间四面透风的破仓房。
那一年,父亲说:“我们家收了生产队累计八年时间才能分给我们的口粮”。
那一年,我知道我再也不用吃粘了上牙又粘下牙的芽面馍馍了,并且可以天天顿顿吃拉条子了。那一年,春节家家户户购置了花花绿绿的各色年货,有些人家还添置了手扶拖拉机。村里置办了全新的社火行头,排练了新社火《太平腰鼓》,鲜艳的红彩绸舞动在乡村的碾场上,鲜红的鞭炮碎屑映红了家家户户的大门,喧天的锣鼓响彻了整个冬天。空气开始甜美起来了,人人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若干年后,我才知道那一年的两年前国家就开始尝试实行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了,简称“包产到户”。
那一年,是我们家乡的春天,也是伟大祖国的春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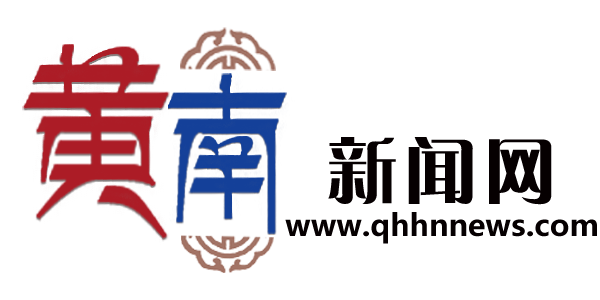

 青公网安备 63232102000018号
青公网安备 63232102000018号